聽特崗教師們講述從教故事、育人感悟——
躬耕山鄉大地 點亮童心夢想
 222
222
“特崗計劃”,全稱為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是國家為改善農村義務教育師資結構、促進教育均衡發展推出的重要政策。從首批特崗教師招聘至今,該計劃已走過20個年頭。20年來,“特崗計劃”已成為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師資補充的核心機制,取得了顯著成效。
在第41個教師節來臨之際,我們走近特崗教師,從他們的講述中感受那份對教育的熱愛、對理想的執著、對職責的信守,並在對“特崗計劃”20年發展歷程的回顧中,共同思考教育的真諦與未來。
雨中的小花傘觸動我心弦
講述人:河南省濮陽市濮陽縣慶祖鎮中心校校長 楊承
2009年,23歲的我從鄭州師范學院畢業,經過層層選拔,成為河南省首批農村特崗教師,被分配到濮陽縣徐鎮鎮黃河灘區的一所小學。
滿懷對三尺講台的熱情,我背上行囊、一路輾轉,來到坐落在小村庄一隅的校園。學校很小,除了五間教室,就是一間簡陋的辦公室。在我來之前,5個班隻有4位教師,每個老師都是包班教學,其中最年輕的一位也已53歲。
雖然有些心理落差,但我暗暗告訴自己:“來就是為奮斗的,不是為享福的。干起來吧!越艱苦的地方,越需要你,也越能發揮自我價值。”
從未獨立生活過的我開始學做飯。學校離集市有十幾裡路,包班教學任務繁忙,我只能趁周末蹭老鄉的車到集市買回一個星期的糧菜。剛到學校的第一年冬天,一場大雪封住了進山的道路,我靠著四個土豆兩棵蔥,硬是熬過了五天。
在教學中,我發現孩子們的課程內容單調老舊,很難激起他們的興趣,便決定在全校開設音體美課。為了不影響其他班教學,體育課場地設在了學校后面小樹林邊上。正是從這片空地開始,學校開始有了體育課堂、拔河比賽、趣味運動會。一系列課程改革,讓校園裡充滿了孩子們的歌聲、笑聲。孤獨感漸漸離我遠去。
是啊,正是孩子們的歡笑聲,讓我不再彷徨﹔是純朴的家長對我的信任與關懷,讓我下決心做得更多、更好。
記得在我剛剛上班的第三周,全縣召開特崗教師交流會。返校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車在黃河大堤上行駛著,天已經完全黑了下來。快到學校時,司機師傅驚喜地高叫一聲:“老師,學生都打著傘到大堤上接您了!”我朝著他所指的方向看去,雨中路邊站著許多打著花花綠綠小傘的孩子,正焦急地向這邊張望。
車停靠路邊,孩子們紛紛跑過來,喊道:“老師,老師,我們以為您不來了”“我們等了您好長時間”“回來就好!這下放心啦”……我沖到車外,抱起最小的一個孩子,眼淚和雨水匯在一起順著我的臉頰往下流……這些點滴瞬間觸動著我的內心,讓我選擇了留下。
2011年9月,學校布局調整,我帶著部分孩子來到黃河大堤另一側的一所小學任教並擔任校長。在這裡,我一邊給孩子們上課,一邊為學校的整體發展摸索嘗試,還抽出課余時間做家訪,傾聽家長們的期待和訴求。
短短兩年,在縣裡的支持下,學校發生了巨大變化:課程齊全了、操場硬化了、校園美化了,教室安裝了網絡班班通教學一體機……先進的教育技術走進校園,讓學生看到了更多山外的精彩。漸漸地,在校學生人數由最初的79人增至300多人。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是教育讓我實現了自己的價值。當年的老同學們各有發展,但我從未“眼紅”,因為我始終相信,自己收獲的,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前路還很漫長,我會為自己的初心而繼續奮斗,讓鄉村的孩子們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多的關懷,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美好明天。
(記者楊颯採訪整理)
在鄉村孩子心裡種下追光的種子
講述人: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勒秀鎮中心小學美術教師 多明靜
我是一名在鄉鎮小學任教5年的美術特崗教師。初到這所鄉鎮學校時,我心裡有對工作的熱情和期待,也摻雜著因陌生環境而產生的迷茫,五味雜陳。初見校長時,他告訴我,學校目前隻有一名美術教師,負責的是學前班,以后就由我來承擔小學美術教學工作了。聽了校長的話,我既興奮又不安。
帶著熱情和期待,我踏上了三尺講台。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接一個挑戰:陌生的工作環境、難懂的方言、淘氣的孩子、教學經驗的不足……我一點點摸索著、一天天進步著。
經過一學期的磨煉和學習,在新教師公開課上,我的教學得到了校領導和同事的肯定和鼓勵,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來自身邊的溫暖。“我們相信你可以的,果然沒走眼”“你的課堂語言很精練!”“這幅剪紙我好喜歡,可以送我做紀念嗎”……一聲聲暖心的話語,一句句耐心的教導,都激勵著我做得更好。不久后,我創設了學校剪紙社團,很受學生歡迎。漸漸地,心裡那種身為教師的責任和快樂,越來越強烈。
教育是心與心的交流,是靈魂與靈魂的碰撞。而美育不僅是對美的感知和欣賞能力的培養,更是一種情操教育和心靈塑造的途徑。剛開始,孩子們對美術課的概念很模糊,於是,我從最基礎的線條和形狀教起。學校沒有足夠的顏料和畫紙,我會買來當小獎品送給孩子們,還帶著孩子們用樹葉、石頭等天然材料作畫。
學校地處洮河之畔,結合大美羚城“恬美勒秀·生態嶺南”的發展定位,2022年,我在校長的指導下創新性地推出了“石頭生態課程”。這一項目式校本課程,將自然環境資源與美術教育相結合,通過“尋石、探石、玩石、繪石、寫石、說石”六個環節,讓學生在實踐中探索石頭的奧秘,感受自然之美,同時提升他們的審美能力、創新能力和人文素養。
那時,班上有個叫完瑪當智的男孩,平時總是沉默寡言,上課也從不主動發言。在一次繪石課上,他把一塊橢圓形的石頭畫成了洮河邊的牦牛,石頭的紋理恰好成了牦牛的絨毛。他低著頭小聲對我說:“老師,這是我爺爺放的那頭老牦牛。”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美術可以讓內向的孩子找到表達的出口。
去年秋天,我帶著孩子們在校園裡採集各種樹葉,教他們用樹葉做拼貼畫。有位家長特意來找我:“多老師,我家丫頭以前總愛撕作業本畫畫,現在天天在院子裡撿葉子,說要做‘會開花的畫’。這都是您教得好啊!”同事們也常會在辦公室裡討論:“多老師帶的孩子,現在看啥都帶著‘畫兒’的眼光了。”我覺得,這些話語,比任何獎狀都讓我感到自豪。
成長之路雖非坦途,卻也並非崎嶇難行。作為特崗教師,或許沒有站在城市講台上的那份光鮮,但我們播下的,不只是藝術的種子,更是點亮鄉村孩子眼睛裡、心靈裡那簇光的火種,這便是在我的特崗歲月裡最沉甸甸也最溫暖的收獲。我在每一個細微的進步中累積,逐漸蝶變,向著更加理想的自己穩步前行。
(記者楊颯、王軒堯採訪整理)
做“紅燭精神”的忠實傳人
講述人:雲南民族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數學教師 趙慶准
金秋9月,又聞琅琅讀書聲。作為陝西師范大學2020屆畢業生,無論是做特崗教師時雲南會澤縣茚旺高級中學的教室,還是如今雲南民族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的校園,都見証了我的選擇:將足跡印在彩雲之南的紅土地上,耕耘於西部基層教育第一線。
還記得最初報名特崗教師時,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會放棄大都市的繁華與機遇,而選擇來到滇東北的一座小縣城?
我想,最深層的原因,還是來自鄉村的我更能深刻理解一位好老師對農村學生而言意味著什麼。我家鄉的同齡人,有的讀到初中、高中就中斷了學業到工地去打工,他們后來非常后悔沒能繼續讀書。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孩子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同時,作為一名師范生,我認為,隻有一代代教育工作者以更加堅毅的目光、更加堅定的步伐站上基層、西部的講台,用實際行動詮釋立德樹人的拳拳之心,才能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幫助孩子們向著理想進發,自己的人生也才能更為豐滿、更有意義。母校的囑托,我始終銘記在心。我要發揚“師大學子,為中華而教”的優良傳統,做“紅燭精神”的忠實傳人。
初到會澤,也曾為這裡的艱苦而感慨。這裡沒有火車站,出入只能靠汽車﹔沒有肯德基、麥當勞,更沒有高薪待遇和豐富的都市生活。走上講台,教學也並不是預想中一帆風順的“雙向奔赴”。所以,我也曾迷茫過、無助過。
幸而有關愛后輩、體恤新人的領導,他們耐心傾聽我的心聲,及時給出具體而細致的建議﹔有亦師亦友的前輩,通過“師徒結對”“新教師匯報課”悉心指導,讓我的教學更加從容平和,看清了提高專業水平的努力方向﹔還有雖調皮但善解人意的孩子們。記得有次我扁桃體發炎,上課聲音有點啞,課間回來后,看到講台上放滿了感冒靈、西瓜霜潤喉片﹔有一次我不小心摔倒,學生下課專門跑到醫務室為我拿來治療跌打損傷的藥﹔還有一次,因為課堂紀律我對孩子們發了火,他們事后認認真真寫了一堆小紙條,裝進一個大袋子送給我,向我道歉……這些,不就是作為教師的幸福感、獲得感嗎?
迎著晨光,踏著暮色﹔寒來暑往,潤物無聲。不知不覺,三載特崗教師生活一晃而過,雖有幾多艱辛和汗水,但更多的是收獲與成長。我想,熱愛可抵歲月漫長。我將繼續提升自身專業素養,提高教學質量,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用手中的粉筆幫助孩子們書寫精彩未來,書寫自己人生的下一個篇章。
(記者周世祥採訪整理)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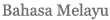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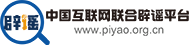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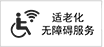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