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精神的具身實踐與具象表達
 222
222
縱觀中華民族文明史,那些被譽為“教育家”的人,都有著躬身化育、成效卓著的教育實踐。中華民族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正是從這些個體的成長經歷、教育實踐中提煉出來的高度濃縮的精華品質。教育家精神的養成與傳承需要具身實踐及具象表達,弘揚教育家精神的關鍵,應落在可見識、可感知、可確認的實處。
具身認知也稱“具體化”,主要指人的生理體驗與心理狀態之間有著強烈的聯系。教育活動本身具有情緒勞動價值,教育過程中發生的情緒是具身化的,具身化的教育實踐會強化教育態度。教育家精神的具身性,要求教育者必須回到教育現場。弘揚和踐行教育家精神,需注重“領悟精神—內化品質—躬身實行”的具象化表達。
其一,以教育激情和信念感塑造具象化師表形象。
心理學上的“激情”是一種源自心理體驗的強烈的情緒狀態,通常指個體出於對活動的熱愛而投入大量時間精力,並將活動轉化為個體身份認同的一部分,表現為個體的強烈偏好傾向。個體對某一活動可能會單純表現出“熱情”,如外在形式上的積極參與,但不一定會有內在的“激情”。如教師參加各級各類教學比賽,可能會被某種心理情緒驅動而擁有“熱情”,但未必因此對教學產生“激情”。因此,心理學上根據個體活動將“激情”分為和諧激情(HP)和強迫激情(OP)兩類。我們亦可根據教育者將教育實踐內化為身份認同的方式差異,認識教育激情對教師的作用。
和諧激情是個體自由從事某項活動的強烈傾向,它產生於經由某項活動完成身份認同的自主性內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因該活動能夠滿足個體的自主、勝任、關系等自我需求,使個體得以自主選擇和決定是否持續參與該項活動。如一個青年學子自主自願選擇就讀師范專業,自覺將職業取向明確為從教為師,在為“成為一個教育者”做准備的過程中,從精神領悟到實踐體認,從整體形象到微觀細節,他總是能找到自己的標杆,自主對標向學,並通過具身實踐去追求預設目標。又如已經擁有數載教育實踐經歷的教師,通過教育“在場”的具身認知和實踐參與,對歷史上和現實中典范教師形象的精神品質有親身感知,能夠激發和強化自身對教育實踐的積極情緒,進而“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在日常工作中能夠深研專業、認真上課、誠意待生、真心護學,在教育實踐中能夠以德化人、文化育人、知能立人。擁有和諧的教育激情,會讓一個教師的具象表達帶有直觀的、可“觸摸”的信念感。同時,和諧的教育激情也會促升教師的主觀獲得感、幸福感以及使命感。
如果個體出於社會認可或個人尊嚴等壓力,不得不參與某項活動,這種壓力會傳導於個體完成身份認同的“控制性內化”過程中,而壓力又會使個體感到“自我控制”的缺失,此時產生的就是強迫激情。強迫激情支配下的教育活動可能會帶動形成某個方向的“熱度”,但同樣會引發熱力加持之上的“失焦”。如果缺少自主的具身體認,缺乏信念感支撐的“教育在場”,僅靠外在的身份稱號或榮譽光環,是難以形塑具象師表的,更遑論培養“教育家精神”。
踐行教育家精神需要擁有和諧激情,如此才能在具身實踐中獲得心理感悟、精神升華,從而通過具象化的教育行為凝聚教育信念,含蘊從“職業”到“事業”的獲得感和自豪感,形塑立體可感的師表形象。
其二,以鏡像認同建立師表形象的具象化表達。
社會中他人的評價、態度等外在因素,都是反映一個人“自我”的一面鏡子。在鏡子中,“他人”不斷向“自我”發出約束信號。在他人的目光中,人們逐漸內化出內在的“自我”,這就是鏡像認同。於教師而言,塑造教師鏡像的“他人”包括“在場”的學生、家長、同行,以及雖然看似“離場”但與教育息息相關的社會全體,教師之所以成為他人認可的教師,就是在具備和保持個體品性的前提下,不斷通過鏡像反射形成自我認同、塑造師表形象。
社會對教師的評價和期望,通過鏡像效應影響教師的自我感覺和行為,教師在與“他人”對話的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內化社會規范、文化意蘊、價值觀念等,形成自我認知,塑造自己的社會身份、建立與世界的關系。如被尊為“萬世師表”的孔子,其教育實踐強調“不學禮無以立”,教育過程將“身”納入,以踐“禮”律己,以“禮”育人,禮為情貌,舉動言行皆由“禮”出,並一以貫之,由己及人,因此子貢嘆稱“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論語·子張》)。在孔子與學生的“對話”中,“師意”鏡像自然塑立,其以身立教、正人正己的垂范表率便彰顯於無形,又進一步塑造和影響其時乃至世代中國人對教育的認知和行為模式。
由史見今,教育家精神品質是“無形中的有形”,隻有經由具身化、具象化,方能入其肌理、悟其奧義。教育者需重視鏡像認同,通過與“他人”的對話獲得反饋,進而具象化塑造並優化師表形象。總之,以具身實踐、具象表達體認中國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保持“教育者在場”,才是新時代教師弘揚優秀傳統的自然路徑。
(作者:馬麗婭,系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教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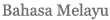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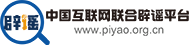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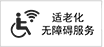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